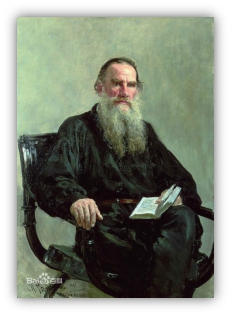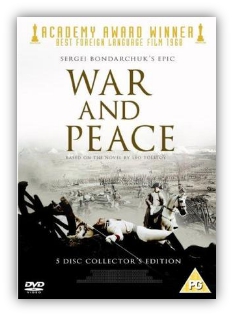1859年4月22日,洪仁玕投奔族兄洪秀全来到南京,仅20天后,洪仁玕即被封为干王,全称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位极人臣虽然只用了20天,但是踏上南京的土地却用了5年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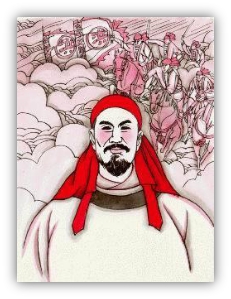
洪仁玕的曲线回归
洪仁玕比洪秀全小九岁,两家分别住在相邻的两个村子,全是洪氏家族,其实二人的关系已经不在五服之内。洪秀全自幼就已聪明过人闻名于乡里,对于这个大自己9岁的哥哥,洪仁玕从小就是极度仰慕的。(中国人最后做粉饰工作,无论是据传教士罗孝全、韩山文等人的记载,还是从洪仁玕的记录来看,洪秀全身上都少不了造神运动的痕迹。)
洪仁玕的科考之路和洪秀全一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为了营生计,兄弟二人都是靠私塾为生。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名落孙山之后,偶然间翻看五六年前获得的《劝世良言》,大彻大悟,解开数年前异梦之谜(打通任督二脉,灵魂出窍般的酸爽)。洪秀全在茅塞顿开之后,首先感化的就是洪仁玕和冯云山。他们做的有鼻子有眼,在河里替自己施洗,然后打倒“孔家店”——毁掉孔子牌位和肖像画。三人更是经常聚在一起研习中译本《圣经》(其疯狂痴迷程度颇像当下的创业小团队)。中国是个乡土社会,几千几百年的传统习惯,在人们的意识中早就构筑起了观念大防,洪仁玕三人的行为早就被乡里视为异端,糊口的营生场所被自己革了命,学生自然早就吓跑被家长另择校了。洪秀全和冯云山是大小伙子了,家里也无法约束,可是洪仁玕毕竟年龄小些,被家长一通胖揍撵回了家。洪仁玕后来又把孔子牌位重新供奉起来,开馆授徒,做回了私塾先生。此间,两位大哥邀他去广西传教,洪仁玕以家有老母为由未能同往。
后来,洪仁玕在家待得久了,也就回到耕读的老路上去了,甚至可以讲,他在跟随洪秀全瞎折腾和科考代表的正途之间出现了犹豫。1850年,洪秀全的传教事业逐渐壮大,更是得益于偶然的土著和客家人械斗,催生出军事力量。洪秀全的宗教活动向政治运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时引起了当地官府的重视,算是正式进了黑名单。这一年,洪秀全在自知即将踏上不归路之后,派人把家里老小接到身边时,曾对洪仁玕发出邀请。可是,洪仁玕苦读经书良久,大考在即,岂能差这临门一脚!更何况,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万一得以高中,岂不是命运来了个大转变。这对读书人是多么大的诱惑。于是,洪仁玕独身一人前往广州应试。
但是,洪仁玕在此期间并不是完全老老实实做个顺民的。他在家乡的这几年,至少发展了五六十名皈依者,给他们一一受洗。1848年冬,洪秀全和冯云山二人回家时,也曾劝说洪仁玕入伙,起兵反清,洪仁玕并没有应允。可以看出洪仁玕的心理肯定是矛盾的——他也想走这条造反的捷径,成功后那就是鸡犬升天的待遇;可是他心底里是不认为两位老兄能成功的,等待他们的只有灭九族的灾祸。洪仁玕还没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
1851年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自封天王。清朝官府一时抓不到他,自然要先把老家给他抓个干净。洪仁玕此时又有了兴致,一路追寻大哥的脚步,却是望尘莫及。为了躲避清兵搜捕,逃难于香港,遇到传教士韩山文。
和韩山文相处了一年时间,洪仁玕给这位传教士讲述了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叛乱缘起。在韩山文看来,这场叛乱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令人惊讶——造反者们竟然举的是基督教的旗(拜上帝会)。韩山文看到了在中国打开传教事业的大门所在。1854年5月,受韩山文资助,洪仁玕企图从香港到达上海,再由上海溯长江而上,穿过清军的防线进入南京。但是事与愿违,洪仁玕在上海待了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实现计划——韩山文的面子太小,外国人的圈子没人买他的账,也就没人肯帮洪仁玕;控制上海县城的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虽然跟太平天国关系不错,可是不相信他是天王洪秀全的亲戚,不施援手。无奈返港,他找到一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助理的工作,一干就是数年。
洪仁玕这几年跟随的传教士是理雅各——苏格兰籍,后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理雅各是个有学识之人,早就对这个所谓耶稣基督之弟——洪秀全不以为然,斥其为异端,更是力劝洪仁玕好好在香港传教,不要回去趟这趟浑水。正如另一位传教士富礼赐在其《天京游记》里评论道:“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梁启超也曾给太平天国做过定性:“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教,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无差异。”

在这世间,有明白人,对应地就有糊涂人或者制造糊涂的人。洪仁玕回到香港写出了《洪秀全来历》、《太平天国起义记》,风行一时,成了有名有姓的人物。香港这个地方的传教士太多了,洪仁玕一出现的地方,总是有人聚拢过来,向他打听中国叛乱的事,有传教士向他灌输一定要去南京,讲真正的基督教带到中国去,带给中国人。因为,他们这些传教士始终没法完成任务,却够执着够投机。
洪仁玕在几年里也确实开阔了眼界,他后来提出的很多经济、政治等纲领,都得益于这几年的学习和见闻。但他心里也想着能够回到已经做大的太平天国去。这一次,洪仁玕偷偷溜出了香港,历经长途跋涉,于1859年来到南京天王府。
洪仁玕的战争岁月
1859年4月22日至1864年11月23日,洪仁玕选择了一条从生到死之路。在此期间,太平天国一面要对抗清朝的围剿,一面要处理与英、法为代表的外国势力或者说是争取外国势力的支持。洪仁玕处于战斗的状态中;当然,时局的发展才不会理睬他有没有准备好。众所周知,洪仁玕来到南京时, 太平天国内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故——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内斗已死,翼王石达开率部远征不归,天王洪秀全猜忌异姓,大肆分封洪氏幼年子弟。天京情况非常不容乐观,南方许多土地已经被清军收复,官军对天京形成包围之势,江南江北两座大营驻扎数万重兵。军事上依靠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侍王李世贤等南征北战。
那么,干王洪仁玕的军事能力如何呢?所谓一战能成名,自然一战也能搞臭。干王在到来20天内一路升迁,虽然李秀成、陈玉成等人一并受封,但是这是拿命换来的。洪仁玕对诸王的不服气心知肚明。或许是出于展示其独特价值的目的,干王提出了解天京之困的“围魏救赵”之法:派军迂回至官军后面,夺取杭州、苏州,抢占官军补给线,迫使江南、江北大营营救,然后太平军再合围并歼灭兵力减弱的两个大营。同时,顺势夺取上海,争取获得洋人的支持,购买洋人汽船,巡视长江并发展海上势力。
干王的战略关键在洋人支持,而他多年的经历和来到南京后的《资政新篇》等一些列改革之举,都深受天王洪秀全的信赖。1860年6月2日,忠王攻下苏州,但是清军曾国荃围攻安庆一年多,到1861年将其攻下,直接威胁天京安危。1860年,以英法为首的列强担心本国利益安危,经过一番斗争后决定保卫上海,由苏州道台吴熙出面,组织华尔召募外国籍亡命徒及军人组成雇佣军阻击太平军。1861年12月29日,忠王李秀成攻克杭州。战事在一城一地之间拉锯胶着。直到1862年2月,英国、法国和华尔洋枪队开始结盟,反对太平军进入上海的天平一下子就倾斜了,太平军的局面急转直下。这背后,其实是英法联军和清政府的短暂利益结盟。至此以后,干王洪仁玕四处搬救兵,诸王都以没有钱粮为由拒绝前往,各顾自己,不顾大局。
总体来讲,干王主持的军事作战多是以战败收场,在具体执行中,与忠王等人分歧较大。他的战争注定了没有赢取和平的那一天。1864年12月23日,洪仁玕在江西南昌遭处决碎尸。
洪仁玕的战争与和平
他的战争注定没有和平。这是洪仁玕的性格弱点所致,也是洪仁玕的能力不及所致。二者又总是纠合在一起的。
英国人富礼赐《天京游记》写道干王:“……盖彼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也。可惜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竦懒,顾面子的自重心及中国人好隐瞒好用术之性常在其人格发展,此皆在干王爽直挚诚之性格展现出来。……在他的特殊地位有一特要的成功要素,即是智慧,可惜他没有;他的自尊自大心毁灭了一切由他的经验而得之知识,鄙俗的歌颂赞扬——由各方面尽量给他的——都不免有相当的恶果。”
智慧与地位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并存关系,多数人是爬到了那个地位,但是智慧不够;而智慧和地位兼而占之一些的,往往不见得能施展开来,会被众俗所吞噬,更何况受命于危难之际。
洪仁玕让我想起托尔斯泰在描写库图佐夫抗击拿破仑的时候的总结。这个能够打赢当时的绝世统帅拿破仑的老头子,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睿智,这种睿智是洞察历史规律的重要能力(库图佐夫的睿智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与他相比,其他的将军则显得庸俗(追名逐利)。
在如此的战乱之际,洪仁玕作为干王,还是享受了纵使和平时期以他的出身也不曾敢想过的奢华——
富礼赐说:到干王府,则见金色与红色互相辉映。府前街上有二亭,亭内常奏音乐不断——乐声有时细微至不足摄耳,但有时嘈响不堪。
……干王约四十五岁,比较胖,有一副开朗、十分快活的容貌。当你见到干王,他会同你握手,用英语说“How do you do?”,并请你就座。
洪仁玕吃饭时,能饮一大杯葡萄酒,同时他在南京城里用西餐招待来访的客人。
桌上陈列光怪陆离形形式式的东西甚多。有一座望远镜(破了),一个枪盒(枪丢了),三支手枪(均生锈的),两盏玻璃灯(不能点着的)……
似乎括号里面的内容更多地隐喻了现实的处境。
题外话——历史的真实
洪仁玕对富礼赐指出了一件事实:如果上海道台对于逃亡的太平军人稍示慈悲宽大而不将其即行斩首,则太平军前线队伍实不容易维系了。
人看见一只将要死去的动物,他会感到恐怖:一个本质与他相同的东西,眼看着将要消灭——再也不存在了。但是正在死亡的是人,而且是亲爱的人,那么,在生命的灭亡面前除了有恐怖感之外,还有感到五脏六腑的撕裂和精神的创伤,这种精神的创伤就像身体的创伤,有时致命,有时痊愈,但是永远疼痛,害怕外界刺激性的抚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