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眼泪
距今有六百多年前的历史上,有这么一号人物——桓温(312年-373年),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也就是历史上的东晋时期,桓温是继曹操、司马懿之后又一有名的权臣。

东晋(317年-420年),是由西晋宗室司马睿南迁后建立起来的政权。该政权维持了长期的偏安统治,疆域大体上局限于淮河、长江流域以南。同时期的北方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先后出现了16个割据政权,故将该时期泛称为十六国。桓温在东晋权力结构的造就下,迅速崛起,并且擅权专政十数年,操纵了皇帝的废立,甚至在最后想要取而代之,自立皇帝。
至于说为什么自立没有成功?有一段流传下来的故事颇为能暴露桓温的性格——
晋太宗简文皇帝司马昱(320年―372年),东晋第八位皇帝。也算的上是权臣桓温所立的傀儡皇帝之一。简文帝整日不敢多言,诚惶诚恐,是不是观看星象,总是担心着某一天就被桓温废去。该来的躲也躲不过去。桓温终于动了废立之心,来找简文帝做思想工作。简文帝等的就是这一天,至少以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在桓温还没开口说话之前,皇帝的眼泪就像南方的雨,一直流个不停。桓温好歹也算是见过血的人,此时面对这个痛哭流涕的场面,不知怎的,双手颤抖,这可是一双最有权势的手啊,冷汗还冒出来,没有留下一句话,转身就走了。

人们都说桓温弱爆了,简直就是妇人之仁的代表啊。桓温为帝不决,枉他雄霸一世还以司马懿自我标榜。其子桓玄称帝后追封了个“宣武皇帝”。
桓温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桓温一生持重,从藩镇到都城建康权力中心,一步步走得可以算得上是稳扎稳打。至于说没有称帝,以“妇人之仁”来解释未免简单了,此事另有原因,这涉及桓温第三次北伐以及东晋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与名士风流
门阀士族,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一个阶层专称。东汉世家地主是其前身,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累世经学,时代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门阀制度形成的标志是九品中正制的实行。门阀政治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兼并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大地主庄园经济的形成,九品中正制保证了政治权力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以军功甚或寒门子弟想要进入权力中枢,真是比登天还难。
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曾经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几家。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谯郡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
而这常青树家族——王氏和谢氏,就是阻止桓温迈出自立一步的关键顾虑。北大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分析说,桓温能够进入东晋权力中枢,也就是都城建康,是在第三次北伐之后。此次北伐,桓温得以据有建康外围徐州、豫州这两个防御重地,这才能够控制简文帝,造成一度“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朝局。然而,桓温的北伐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原因在于枋头战败,使得桓温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以及声望(又是一个特别重视声誉的时代)全方位受到损害,地位在开始走下坡路。也许,有人要问了:桓温的实力这么脆弱,不堪一击?事实上,桓温的实力还真就不够硬气——桓氏一族,出自谯郡龙亢,可谓是族单势孤,族中无人才,朝中无人,只有桓温在外围逐步发展。不像是其他名门望族,兄弟众多不说,都是名重一时之士,在朝廷内外官居要职,家族势力相当庞大。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皆是如此。

东晋历史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历史上皇权到了最低点,而门阀士族权力却在最高点,形成了司马氏(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的局面。在朝廷内外枝繁叶茂的王、谢就是反抗力量,也是名实具损的桓温不敢轻举易动的忌惮所在。王、谢发动自己的力量,以图维护东晋司马氏的帝位。王夫之曾说:“桓温有枋头之败,故王、谢得持之以从容。”
魏晋名士风流,都是受了政治大环境日益恶劣,选择逃避现实、放任自然的人物。名士好玄学和清议,内容空泛,就像是清汤寡水,食之无味。这些人物,一般都喜欢服用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整天谈论的都是有无、才性、出处等等。名士在政治上服膺于“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在山林之中”这样的言论。避世思想明显。士族名士如此这般废事功,轻视武力,统治权力自然要受到不断的威胁。这是后话,魏晋玄学、名士兴盛之时,这就是潮流和时尚,反倒是很多出身不好的人物,想要凭借玄学,挤破脑袋跻身上流社会。桓温就是其中一位。

可惜的是,桓温追慕清名,而清名是真正以门阀高低而论的贵族,桓氏一族却是以事功晋身的,始终为门阀不耻。
桓氏一族
寒门最明显体现其社会地位低下的就是没有族谱可言,也没有祖产祖庙用以供奉祖先。《桓玄传》:“曾祖以上名位不显。”(桓玄即桓温之子)桓氏一族出自谯郡龙亢,西晋八王之乱后桓彝,也就是桓温的父亲,南渡建康,与东晋执政的世家大族相比,门户地位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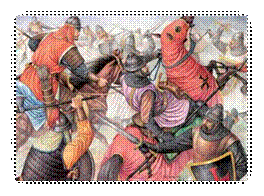
桓彝在桓氏一族南渡崛起中起了奠基作用。简单说来,桓彝在八王之乱时,就曾有反对乱贼的义举,后来南渡归入东晋政权,留心时用,志在立功建业,寻求仕途上上升的机会,以巩固提高门户地位。桓彝的努力是成功,南渡后没有几年工夫,就居于名臣之列,“莅官称职,名显朝廷”。桓彝之所以选择这么一条事功之路,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的门资不足以显贵,与门阀士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有没有半点关系,附庸风雅不是他这个家族该做的。
桓彝南渡时年近四十。经过苦心经营,虽然立功受爵提高了家族地位,但是家族人丁稀少,仍然是势单力薄,为江左门阀所轻视。桓温接过了家族重担,其实到其死时,家族地位也没有根本改变。可见,门阀士族界限森严。桓温也是从行伍出身开始其政治征程的。在魏晋时代,“兵”这个身份的指代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兵卒的身份极其低下。这就像胎记一样,从桓温一出生就落在他的身上了。
但是时代的风尚就是谈玄和以名士标榜。桓温也一直在向主流靠拢,奈何融入另一种阶层却是异常艰难。《太平御览》记载:“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马持矟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就是在讲,桓温与殷浩、刘惔谈玄,谈那些有无、名教与自然什么的,学问底气拼不过人家,一怒之下,叫下人拿来武器,耀武扬威一番,这才出了这口低人一等的恶气。逞了一回匹夫之勇。
到了永和年间,桓温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方镇势力,占据荆州、梁州之地。在朝廷内部,桓温得到辅政何充提拔,“当今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此后,桓温步步为营,吞并豫州、江州、徐州、兖州,三次北伐,进而进驻权力中心建康,差一点做了篡位的“二十分贼”。
桓温至死,都没有迈出篡位称帝的最后一步。死后,其幼子桓玄承袭其封爵,此子与其父颇像,慢慢成长为东晋权臣,历任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徐州刺史、相国、大将军等职,封楚王。桓玄消灭殷仲堪和杨佺期,占据荆、江广大土地,最后消灭掌握朝政之司马道子父子,掌握朝权。大亨元年(403年)12月逼晋安帝禅位于己,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桓楚,改元“永始”。至此,桓温没有做到的事情,其子桓玄帮助其迈出了这一步。桓氏一族也算是踏入顶峰。这其中,颇有几分被迫走上篡位道路的辛酸——
桓玄五岁承袭其父的爵位,少不更事。待其长大成人,相貌、神态颇像其父,博通艺术,善写文章,兼具风流与英雄气概,自己也颇为得意。然而由于其父桓温晚年有篡位的迹象,所以朝廷一直对他深怀戒心而不敢任用。到了二十三岁,桓玄才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几年后出京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太守,作为权臣之子的桓玄颇觉不得志,曾感叹:“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就弃官回到其封国南郡(今湖北江陵),也就是他的袭爵封地。途中经过都城建康,拜见执政的宰相司马道子,司马道子酒喝多了,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你父亲桓温晚年想当贼,你怎么看?”突发其问,场面颇为尴尬。桓玄跪地流汗不起。由此可以略微窥知,桓温有篡位之心之事,对其子桓玄的人生命运有着幽暗的影响,当年要是心狠一些篡了位,今天也就没人敢指着鼻子说三道四了,反倒是这般苟且,活的不痛快。
“英雄”慕“风流”
东晋著名清谈家、出身世宦之家的刘惔称桓温:“须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孙权、司马懿之流,都是当世英雄人物,建立了自家政权。桓温在《世说新语》中得入《容止》篇。可以想见,桓温不但有英雄器宇,而且相貌也英伟。
同时,桓温还颇通谈义,与刘惔、殷浩这样的风流名士交好,又与寻常武夫可比。此中心态和纠结,前文也有提及。《世说新语》还有一记录,表现了桓温这位英雄人物的名士风流:桓温北伐经过金城时,见到此前为执掌琅琊时亲手所种的柳树,现在已经有两手合围之粗,不禁生了感慨,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折下柳条来,痛哭流涕。
东晋那个年代,应当说是“名士”引领风骚百年的时代,社会风尚为之导引。“英雄”风貌是其追随者,但也别有一番天地,如桓温这般人物就是引领“英雄”风貌的人物,给名士风流添了几分勃然英气。这般人物,还有大家广为熟知的曹孟德——曹操,能文能武,英雄气概沛然发露,“床头捉到人,此乃英雄也!”
声明:凯风文化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智见往期:《清初亲王吴克善的“女人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