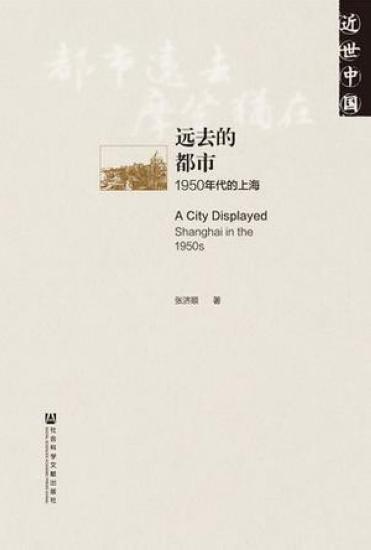
张济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
今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新书出版。她在书中从里弄、影院、报业、大学等社会文化微观层面探讨解放初期上海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重访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文化。在张济顺看来,1950年代的上海在经历天翻地覆大转折的时候,其文化、观念、习俗也延续着某些惯性的东西。
日前,该书出版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哈佛大学荣退教授傅高义、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裴宜理、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陈兼、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杰出教授贺萧、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许继霖、姜进等多位该领域重要学者参与了座谈,围绕“断裂与延续:共和国史研究再思考”的话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次活动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主办,腾讯思享会报道。

1950年代的上海断裂和延续交织
张济顺新著出版半年以来,学界在有关此书的讨论方面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是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那就是1949年是不是中国历史的断裂。张济顺当天的发言也围绕着“断裂与延续”的话题,讨论“断裂”与“延续”各自的表现和交互的作用。
至于选择1949年这个节点,张济顺表示是指向了三种将1949年视为历史鸿沟的叙事:首先是以政权交替为主线的红色叙述,在这种所谓的革命史叙述中,1949年前后的社会是截然分开的;其次是集权主义的黑色叙述,这种叙述讲述的是国家吞食社会的过程,自然认为1950年代的上海中断了都市地方性的脉络;最后是革命和摩登的对立史观,即所谓的粉色叙事,就像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所写的,把上海1949到1979年的历史视为和摩登完全对立的时代。在张济顺看来,1949年前后的上海社会依然存在着隐秘的联系,并且和明显的断裂同样重要。二者的交织进行,使得1950年代的上海呈现出“革命和摩登并存”的状态。
对于这本书所要着力展示的“断裂之下的非断裂”,张济顺列举了三个方面的表现:旧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还在,构成社会最底层的基底性的东西还在;被革命所浸润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还在;国家“入场”而都市“在场”构成了1950年代上海的历史主题。
张济顺认为1950年代的上海是在革命和摩登的张力当中来显现出断裂与延续这个复杂的场景,因此,在这个年代中,“任何一种摩登都脱不去革命的外衣,而任何一次革命,哪怕是触及灵魂的革命也洗不尽摩登的铅华。”
广大的农民不能成为现代化的被遗弃者
姜义华对张济顺提到的国家“入场”都市“在场”的模式做出了回应。姜义华认为对此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在他看来,1949年的革命是在广大的农村中间壮大起来的,共产党对组织农民、发动农民非常熟悉,但对于管理上海这样一座大城市是缺乏经验的。“因为长时间扎根于一般是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都相对单一的中国,我们形成了依靠国家看得见的手,自上而下实现动员和管理的模式。上海市民跟中国广大农村的农民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在上海应当说主要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多样多元的东西共生共存的,而且相互不断地博弈、渗透。”因此,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农民的文化和现代都市现代化在这里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
姜义华认为,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上海国际大都市,中心问题还是要实现现代农民运动和现代化运动的有机结合,防止二者相悖,“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让广大的农民不断地从现代化发展中得以实际的利益,他们不能成为现代化的被遗弃者,这是中国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的意义超过1949年和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
傅高义在讲话中则提出了上海特色的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傅高义研究过广州,认为广州的情况和上海有相同的地方,虽然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和对外的摩登的程度超过了广州,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这些也随着社会层面的延续而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共产党来了以后有这么多运动?开始有一个思想教育的运动,还有三反五反,还有很多百花齐放,还有反右运动。因为社会的结构变化不满足全国的情况。他们本来的思想还在,虽然开展了很多运动,但还没有根本改变。”
所以对于50年代的意义,傅高义认为比不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学者,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地方与全世界开放的联络以及市场经济改变对了中国人的生活和视野。“1978年改革开放,是对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结构都改变了,有点超过1949年,也包括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遗产是什么?
裴宜理认为张济顺著作的意义超出了个案研究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个关于革命如何影响社会文化变革的独到视角。裴宜理对于张济顺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问题颇感兴趣,就是人们在当代的上海怀念过去的上海,反映的是不是不仅是对30年代上海摩登的向往,同时是不是也在怀念文革以前的新政府刚刚建立起来之后的50年代的上海?裴宜理认为通过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许多重要话题,“50年代上海留下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遗产?50年代和之后的文革10年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中国在大跃进后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不是在近20年之后才实行的,那中国的今天会有什么不同?”
另外,裴宜理也对书中章节作了解读。其中一章描写了教育背景差不多的两兄弟对革命政策不同的反应。裴宜理认为这说明了个人性格的重要性,“分析大规模的社会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也不能忽略个人性格的影响和作用。”
同时,裴宜理提出了圣约翰大学或者其他的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的遗产是什么的问题,“他们当然有很多有名的校友,比如说荣毅仁等,但除了这些校友之外,全球化的模式有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没有中国的1949年就没有1978年
陈兼指出当我们在讲到摩登这些概念的时候,不仅需要一种在场感,同时还要有一种历史的演变感。“也就是说不管你在多大的程度上,用各种经验、资源创造出一种似乎和过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一种新的摩登,在那种情况下,它仍然带上了作为创造者他们自己的想象、动员、参与、改造,到最后成型。”在陈兼看来,1949年之后的摩登虽然和30年代有联系,但更多的是一种有新中国色彩的摩登。
对于傅高义提出的1949年和1978年的历史意义的问题,陈兼说,“我不想挑战您,您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但是没有中国的1949年就没有中国的1978年。”
陈兼认为共和国历史重要的不是对错的问题,而要说的是究竟在哪个地方、哪些地方走上了岔路,如何因此会走上岔路,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有意思的是,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共和国仍然为1978年的到来留下空间和余地,在很多方面,它的正面的甚至包括它负面的经历最后仍然使得1978年成为可能。”
1950年代上海的历次运动未能达成既定目标
杨奎松认可张济顺在书中有比较强调延续,而不是断裂,“这个跟我的对现当代史的看法有一点差距。”在他看来,笼统地说以断裂为主还是以延续为主都无法讲清楚1950年代的中国,“社会层面毫无疑问延续是主要的,政治制度层面毫无疑问断裂是主要的。”
“195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在这个历史背景里头会有很强烈的断裂感,政权改变了,制度改变了,但这个社会没有改变。因为对社会的改变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长。”
所以,“共产党想推行它整套的制度改造,社会的改造,思想的改造,但很难做到。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把农民吸引过来,而实际上农民当中所通行的整套规则和规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他不会为了革命而放弃一切。所以干部,包括共产党的政权都必须要迁就农民在转变过程中的过渡。”在杨奎松看来,中共在上海五十年代在每次运动当中都没有真正达到开始设计的目标,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包括社会当中的人没有办法完全适应。
党国体制扼杀处于萌芽状态的上海市民社会
姜进认为张济顺在书里的都市和摩登基本上是等同的,“也许可以更加细化一下都市和摩登。再讲开的话,不光是一个定义的问题,牵涉到什么是都市,什么是摩登?究竟远去的是什么东西?”
谈到城市研究的话题,在姜进看来,中国历史上有城市,但是没有韦伯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城市自治,但是却有蔚为壮观的都市文化现象。“城市自治整体来说就算有的话,也不是很强大的,还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儒家的政治体系。但是都市、摩登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早就存在了。”
据此,姜进认为远去的是都市繁华而不是城市自治,“民国上海也没有自治,有都市的现代化治理,但是没有现代化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它只能是萌芽状态。”而且,民国时期萌芽状态的上海市民社会其实到1945年以后就是在不断被扼杀的过程中,到1949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市民社会。

上海通过隐秘方式改造新来的文化
许继霖对张济顺提出的“三色叙事”的说法非常欣赏。在他看来,红色叙事强调革命,黑色叙述强调集权,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但其实它们的背后有同构的东西,就是“相信政治力量无所不在,而且有巨大的未来。”
许继霖认为“无论是红色还是黑色的,50年代的上海的确是被一套新的政治力量改造。”但他同时也提出改造之外有更重要的反改造:城市和社会怎么在抵抗政治。因为“上海从晚清以后一直是社会中心。虽然1949年以后有一个大的变化,一个新的政权,新的意识形态来了,但社会依然在这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了抵抗”。新政权在改造上海这座城市,但同时这座城市也是通过隐秘的方式来改造新来的统治者和新来的文化。对此,许继霖举了上海女孩穿军装的例子,“即使像文革这么一个极端的时期,当时军装是最流行的服装。同样穿军装,但上海女孩就会把腰身缝一下,显出身材。”
上海人有资产阶级情结?
金光耀指出张济顺研究的虽然是社会史、文化史,但她关照的是那个时代大的政治,试图解答新政权如何通过革命来重构这个社会以及民众如何在新政权的重构中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在他看来,20世纪在中国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1949年-1976年更是革命进入高潮的年代,“那个年代如果不讲政治的话,很难讲得清楚。”
金光耀对于书中的一个说法颇有感慨,就是上海的社会政治文化中间潜藏着一种资产阶级情结。他认为这个说法非常深刻,但比较可惜的是,书中没有选一个能够展现资产阶级情结的个案。在他看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上海有所谓的城市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尽管政治话语讲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但如果放到当时的生活中间去看的话,上海人确实有资产阶级情结。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那些小孩,看到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小孩,虽然政治上感到自己很优越,但心里至少有一种羡慕。”
社会环境的演化相对于政权更替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贺萧在发言中讨论了上海的里弄改造的问题。他说,“共产党可能花了六年多的功夫在里弄建立一个符合政治可靠性标准的地方治理的形式,这个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国家政权在上海有所改变,这并不是说一下子它会在下面改变一切。社会环境变化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一个由可靠的干部群众组成的居委会发展起来之前,共产党实际上是通过很多在政治方面不太可靠的人,比如说原来帮会的人,道门的徒弟,在里弄成功改变了日常生活。
贺萧认为上海这个都市并不是全部一步一步地一起往一个方向走,“有的走的慢有的走的快,有的往前走,有的往后退,有的简直不动等等”。因此,如果要继续研究上海的都市演变过程,必须使用细致的分析方法,其如是说。
更多精彩:《凯风智见:两大“影帝”飚戏成就清代满蒙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