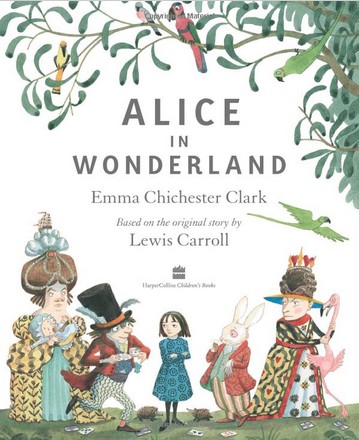
网络图
今年是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二十世纪“圣经之外被引用最多的英语书”)出版一百五十周年。这位牛津数学系鬼才教授在《漫游仙境》及其续集《镜中奇遇》中塑造了两个交相辉映的疯人乌托邦,这乌托邦同时是朝圣地、诊所和炼狱,既是世界尽头又是冷酷仙境。在那里,形形色色的疯人在同一个昏冥不定的边缘线上翩翩起舞,在亚当做第一个人类之梦之前,他们就开始为自己的嘉年华交杯痛饮。在“仙境”和“镜中”,常识(common sense)让位给普遍的荒诞(common nonsense),可确诊的疯癫让位给暧昧而难以定罪的疯狂。只是,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困住小爱丽丝的其实是两个水上乌托邦。
十五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和绘画里集中出现了一个较新的意象:一艘装满疯人的大帆船。关于疯人船出航的目的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一场驱逐,旨在将无法在常人中栖身的疯子送往远方的精神病院,或一个贺拉斯式的安提库拉(盛产药草的希腊城邦);也有人将它看做奥德赛之航,甲板上的疯人都是出发去寻找理性的朝圣者。关于这一主题,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塞巴斯蒂安·布朗特用德语写就的《疯人船》。布朗特之后的同主题作品层出不穷,福柯曾在《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一章里开出一个长长的书单。福柯认为用船只运走疯人的做法有充足的历史根据:早在布朗特之前,从荷兰到奥地利的欧洲城市居民登记档案里就有对这类遣送的记载,而航行的目的地既有原先的宗教朝圣地(圣马替兰、圣伊德维尔、柏桑松、吉尔),也有远非宗教重镇的城市——这些城市成为了所谓的“反朝圣地”,病人只是被简单粗暴地遗弃,好让他们的来源地得到净化。
不难注意到卡罗尔笔下“仙境”和“镜中世界”与这些城市之间的相似。一方面,仙境和镜中是疯人的天堂,他们不必为自己的“反常”感到自卑,倒是颇有一股气势凌人的优越感,表现在毛毛虫、柴郡猫和蛋头(Humpty-Dumpty)身上,就是对侵入者爱丽丝的颐指气使。另一方面,居民又并非全然心甘情愿地遵从那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而违规者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仿佛“仙境”和“镜中世界”是两座机关遍布的炼狱,其中的疯人必须为证明自己配得上重获理性而经受重重考验。表面看来,“仙境”中的立法者是红心王后,“镜中世界”里则是红王后和白王后——相比之下,两本书中的三位国王成了无足轻重的装饰,不是逆来顺受就是完全噤声——然而王后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监狱中的囚徒,和她们的臣民一样,是被看不见的疯狂之巨手肆意把玩的乐高玩具。在这有着仙境外表的炼狱里,所有人都在努力挣扎着从一场深梦中苏醒,而这炼狱里无火光,亦无刀剑,乃是水之狱。
想想是什么把我们引入这疯人的乌托邦?爱丽丝的故事诞生于一次水上的旅行,水为叙述者提供灵感,而故事也是在水面上初次被说出口的。事实上,《仙境》一书始于一首关于航行的小诗,其第一节如下:“一切都发生在金色的午后/ 我们悠悠地在水面漫游;小小的臂膀笨拙地/ 划动我们的双桨, / 而小小的手儿还在假装/ 指引我们的漫游。”《镜中》则以一首关于航行的诗收尾:“阳光明媚的天空下,一叶小舟/ 做着梦般向前泳动/ 那是七月的傍晚…… / 永远沿着溪流向下漂移/ 永远在金色微光里徘徊/ 生命,难道不就是一场幻梦?”卡罗尔对“水上的漂浮”这一意象深深沉迷,在欧洲文学的集体潜意识中,躁动的水永远和疯狂密不可分。疯狂仿佛是展现在人体内的一种浑浊水质,它无序、混沌、昏昏欲睡,是稳健和有条理的心智的反面。
水也是由生者之国通往死者之国的中介。加斯东·巴什拉在《水与梦——论物质的想象》中为我们比较了卡翁情结和奥菲莉娅情结:“动身走,这就是死一点”,各条大河都是死者之河。拜占庭史学家普洛科普说:“他们负责往那里运送死魂灵……在岸边看到外来的船只,船上却无人,可是船似乎沉重无比,像要沉没一般,仅仅高出水面一指。”布列塔尼的古老传说里总有幽灵舟驶过:“这些船只长大得很快,不用几年时间,一艘沿海航行的小船便长成一艘庞大的双桅帆船。”这些逐渐膨胀的船只总是由一位希腊神话中冥河艄公卡翁式的满面愁苦的老人掌舵,总是不堪负荷般地濒临沉没,终点总是地狱。圣梯纳说得好:“无卡翁,便无地狱可言。”
卡翁情结及其变体同样迷惑着卡罗尔。《仙境》故事的第一幕就在河岸边展开:姐姐正阅读一本无图画的书,身边倚着百无聊赖的爱丽丝。接着,第二章中出现了眼泪池,变小的爱丽丝不慎滑落其中,不得不努力游到岸边——岸上等待她的是一群疯狂的动物。在《镜中》第五章中,爱丽丝来到一家幽暗的商店,店主老绵羊正用十四副棒针织毛衣,爱丽丝接过其中一副棒针,它们却立刻变成了一对桨——转眼间她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条小舟,下方是湍急的河流,于是只好用这对桨划起船来,而在航行的终点等待她的是圆胖高——水永远将爱丽丝和读者一起引入更深沉的疯狂中。
“航行的实用性并不是足够的明晰,以至会使史前人凿木造舟。任何一种实用性都无法为航行的巨大风险作辩解。要敢于远航,就必然有重大利益驱使。然而,真正的重大利益是空幻的利益。这是人想象出来的利益……虚构臆造的利益。”巴什拉关于航行的宣言不仅适用于史前人,也适用于一切握起笔、准备讲述故事的人。一个半世纪前,卡罗尔与小爱丽丝在牛津附近的金色池塘上荡桨的那个下午,或许也曾感受到同一种微光灼烁的诱引。
更多精彩:《凯风智见:两大“影帝”飚戏成就清代满蒙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