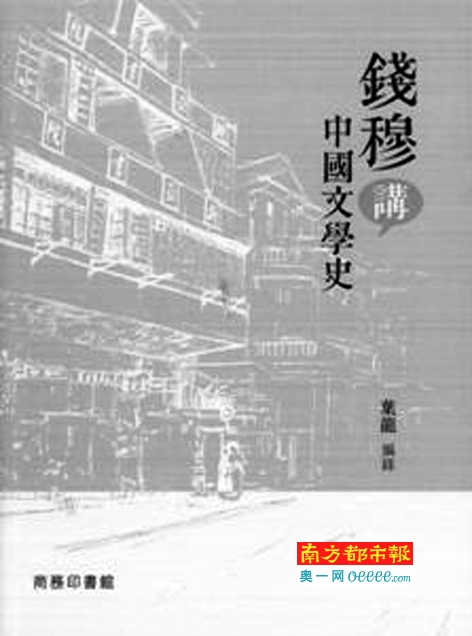
《钱穆讲中国文学史》,叶龙编录,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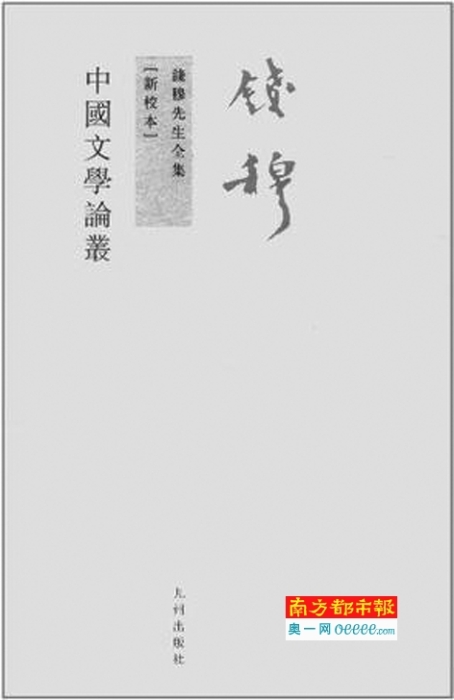
《中国文学论丛》,钱穆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版。
钱穆先生是史学家、思想史家,于文学,不可谓专精。但他对文学自有一番解悟,亦自有其深刻动人处,这方面的文章均已收入《中国文学论丛》一书。今年,香港的叶龙先生将他在新亚书院从学于钱穆先生时所记录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整理出版,题曰《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讲义记录的起讫时间为1955年秋至1956年夏,从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一直讲至明清小说,乃至新文学,是对中国文学的一次概观。其内容与《中国文学论丛》相表里,有些地方讲得深入些,有些则属于泛泛而谈,然终不失为反映钱穆先生文学见解的有价值的资料。
下面拟按时代先后,将我认为《钱穆讲中国文学史》中最值得留意之处略加评介,尤其是尽量与《中国文学论丛》中的相关表述相对照。
一
钱穆讲《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谓:“这首诗是讲古人打仗,但与西方荷马史诗之风格意境完全不同。‘思’是一声符,即沪语‘ 哉’之意。至于这里的‘ 雨’字,可作名词或动词用,但‘ 依依’两字,今日实在无法译成较妥当的白话。‘杨柳’代表惜别之意有三千多年,树枝摇动有亲近之意,可以说,西方并没有如此传统的文化。中国三千年之古典文化,其简明有如此者。”(第4页)又谓:“此诗并非专说时令与自然,乃将自己心情与大自然融化合一,虽是赋,但其实却含有比与兴的意义在内。此即将人生与自然打成一片。从其内部说,这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性灵,从其外部说,这是诗的境界。”(第7页)讲义中文字,原不必字字吹求,但取其大意可也。且对比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的讲法:“此两语,除‘ 思’字外,‘ 依依’‘霏霏’四字,须稍经阐释,而此两千五百年以前之一节绝妙文辞,其情景,其意象,直令在两千五百年以下之一个十一二龄之幼稚学生,亦可了解,如在目前,抑不啻若自其口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窃以为,此处须注意者在“‘依依’无法译成白话”之说。中国文学之美,其来源,至少部分地在中国之语汇。“杨柳依依”,无论做何种白话翻译(或译为他种语文),均无法获得其原有的美,原由何在?其实就只在那字面上。换一个角度说,此种字面,亦为中国人的审美基因,我们以之为美,乃因我们对美的原初观念恰是从这种基因里生发而来。“杨柳依依”树立了一种审美典范,说它美,好比说尺子是直的,实等于没说了。
钱穆的文学观,范围较广,《尚书》、《春秋》、《论语》、诸子,他也看作文学。他讲《论语》“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章,谓:“孔子这段话,充满着诗情画意……前三句均是在描写一‘穷’字,实含有画意;最后两句实含有诗意,这是诗人的胸襟,这叫吐属……如‘浮云’两字不论何处人均可会意,实有其意境,人人可明白,故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无韵的散文诗。”(第17页)且看《中国文学论丛》中对这一章的解说:“此章也是直叙赋体,若在‘乐亦在其中矣’一句上截住,便不算是文学作品了。但本章末尾,忽然加上一掉,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掉,便是运用比兴,犹如画龙点睛,使全章文气都飞动了。超乎象外,多好的神韵。因此此一章亦遂成为极佳的文学小品。”(《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钱穆所说,实为一种文学意味,即令应用文、学术文中亦可有此种意味。当然,只要富此意味者,即视为文学,这样的文学观,便是范围较广的文学观了。顺便说一句,钱穆课堂上讲这一章,似比《中国文学论丛》里自己写的要好。
二
文学史各阶段中,钱穆对建安文学极激赏,于魏武、魏文二帝尤称扬不置。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观念甚合钱穆之思想,以至于他说:“曹丕的《论文》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为中国文学史上之呼声……曹丕才是真正的文学家,能看出文学之价值。”(第68-69页)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也曾写道:“中国文学的确立,应自三国时代曹氏父子起。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正式的文学批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关键。因文学独立的观念,至此始确立。”(《中国散文》)按,民国学者盛称曹丕之文学造诣的,实不止钱穆一位。《顾随讲〈文选〉》一书记录顾随之语:“魏文帝曹丕———中国文学批评与散文之开山大师……中国散文家内,古今之中无一人感觉如文帝之锐敏,而感情又如此其热烈者……文帝感觉锐敏、感情热烈,而理智又非常发达。人欲成一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此三条件必须具备。”(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46页、第57页)尽管角度不尽相同,钱穆、顾随对文帝才华的推崇则一,这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谈魏武、魏文二帝,钱穆尚有一段极妙的评语:“……此种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说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谈的都是没有价值的,却生出了价值。”(第92页)此语隽永,愈思愈觉有味。
唐代文学家,钱穆推崇的是杜甫和韩愈,他说“退之之文变化无穷”,诸体兼善,说得很对。韩愈确为中国散文之高峰。钱穆着意讲了韩愈的一些小文章,并谓:“退之所创的‘赠序’散文,显然是以诗为文,其文章可称为散文诗,是纯文学的,文中的情味,非议论,亦非奏议、碑志,是无韵的散文诗……这是退之独创的诗体散文,是抒情文。”(第138页)这个“无韵的散文诗”的提法,钱穆自己似非常得意,曾在不止一个地方重述过。在《中国散文》一文中,他写道:“……又如韩愈《送杨少尹序》之类,此可谓是一种无韵的散文诗。韩愈于此等散文,本是拿来当诗用,这实在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大变化……散文在纯文学中之地位崇高,其功当首推韩愈。”在《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一文中又谓:“唐人喜欢写诗赠人,韩昌黎改用赠序和书札等,外形是散文,内情则是诗,是小品的散文诗。我常说韩文很多可称是散文诗,其实清代文学家早就说过。清人认为韩愈的《题李生壁》,是一首无韵之诗,那便是说它是一篇散文诗了。”此处所谓“清人”,是指曾国藩,其评《题李生壁》,曰:“低回唱叹,深远不尽,无韵之诗也。”
钱穆于《红楼梦》与新文学,皆不能全心全意地欣赏。《红楼梦》,承认它“描写十分细腻”,但重点在说它“是闭门写作的”、“是规规矩矩的”、“事情少,是文胜于事”(第182、第183页)。《中国文学论丛》里的讲法则是:“《红楼梦》仅描写当时满洲人家庭之腐败堕落,有感慨,无寄托。”(《中国文学史概观》)钱穆认为不如《水浒传》。关于鲁迅,钱穆说:“中国有两位用白话文骂人的,除鲁迅外,尚有稚晖……鲁迅骂人的文章,对青年人的影响很大,吴稚晖的文章粗俗,鲁迅的则尖酸刻薄而俏皮,但平心而论,其《呐喊》集中的小说写得很好……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但他的尖酸刻薄体裁是否可流传后世,则是一大问题。”(第178- 179页)然须留意的是,钱穆对《呐喊》的赞许,着眼点颇与众不同,可参照《中国文学论丛》中所述:“五四以来,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满篇杀伐之气,否则是讥笑刻薄,因此全无好文章。即如小说、戏剧等,平心而论,至今亦尚少几本真好的。只有鲁迅。但鲁迅最好的也是他的小品。像他的《呐喊》之类,这和西方小说不同,还是中国小品文传统。”(《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
三
全书显露钱穆襟怀处不多。讲汉赋时,他说:“扬雄后欲学效儒者,著《法言》,又著《太玄》,扬见当时政治实况大变,放下帘寂寂草玄,桓谭对他说:‘你这本书我读不懂。’扬回答道:‘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第35页)钱穆甚爱此语,曾多次引用阐释。如《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扬雄“尝草《太玄》,人讥其艰深,世无好者,谓仅可覆酱瓶。雄言,无害也。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并加以发挥:“此一语,始启以下文学价值可以独立自存之一种新觉醒……此种文学不朽观,下演迄于杜甫,益臻深挚。其诗曰:‘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世无好者,乃始有饿死之忧,然无害也。至于后世是否仍有杜子美,亦可不计……此种精神,几等于一种宗教精神,所谓‘推诸四海而皆准,质诸天地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中国文化体系中本无宗教,然此种自信精神,实为中国文化一向所重视之人文修养之一种至高境界,可与其他民族之宗教信仰等视并观。”《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一文亦云:“所谓藏诸名山,传诸其人,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此乃中土所尚。因其文学萌茁于大环境,作者所要求欣赏其作品之对象,不在其近身之四围,而在辽阔之远方……人不知而不愠,以求知者知。钟子期之与郢人,有遥期之于千里之外者,有遥期之于百年之后者。方扬子云之在西蜀,知有司马相如耳。故司马赋子虚、上林,而彼即赋长杨、羽猎。及久住长安,心则悔之,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于是草《太玄》模《周易》,曰:‘后世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其所慕效者在前世,其所期望者在后世。下帘寂寂,斯无憾焉。”在讲义中,钱穆有一段话,说得很好,与他文章中所写呼应:“中国文学史带有教训性的,是上层的,政治的,内向型的,且不必一定求人了解,是阳春白雪,别人不懂欣赏亦不在乎……抱着‘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态度。中国文学是传下去的,是等待后人发掘欣赏的,数千年前的文章,今日仍可诵读。”(第64页)。“草玄”者,实为钱穆的一种自况。当时,他困处香港一隅,亦可谓“下帘寂寂”了;“其所慕效者在前世,其所期望者在后世”一说,也是他自我开解的一种方式。其襟怀与抱负,于此小露峥嵘耳。
在讲授者身后整理的讲义,往往不能完整呈现讲授者的精神与深度,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钱穆讲中国文学史》书中颇有些部分令人疑心并非讲座时的原貌,但无法深究,亦无须深究了。至于鲁鱼亥豕之处,自不能免,如《域外小说集》误为《城外小说集》(第184页)之类,可以勿论,有些地方却费人思量。比如讲《诗品》一段,说“钟嵘认为曹操的作品只是下品,将陆游评为中品,实在有点偏见”(第73页),这样关公战秦琼,当然不可能。那“陆游”的位置上到底该是谁呢?想了想,莫非是陶潜———两个字的偏旁跟“陆游”一样?
更多精彩:《凯风智见:两大“影帝”飚戏成就清代满蒙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