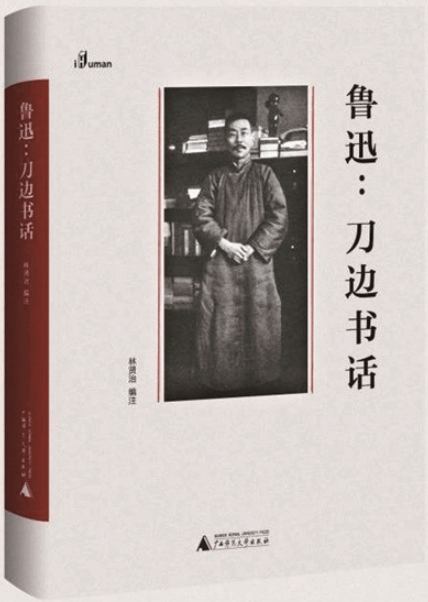
“带着枷锁的跳舞” 《鲁迅:刀边书话》
“带着枷锁的跳舞” 《鲁迅:刀边书话》
天下网商 · 2022-09-02 来源:腾讯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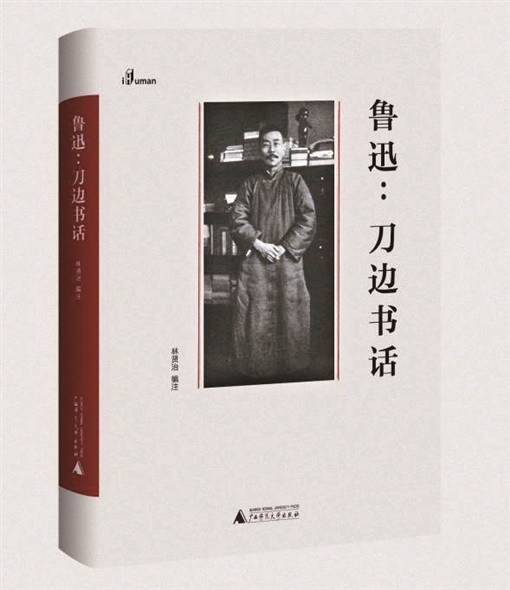
林贤治
早在留学日本时,鲁迅便决心弃医从文,走“摩罗诗人”的道路,把自己置于反抗者的位置上。这样,他一生遭受权力者和专制政治的压迫,势所必然。
在北京,继女师大风潮之后,鲁迅介入了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从形式上看,可称“私人论战”。及至上海,国民党的“党国”开始建立,在“一党专政”之下,他所面临的已是意识形态控制日趋严密的局面了。
在书报审查制度下,鲁迅受到的威胁,远远超出北京时期。在他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写作困境:“遇见我的文章,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最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
鲁迅一直提倡韧战,对反抗斗争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然而,禁锢与压迫的严酷,仍然超乎他的预想。这对一个“精神战士”的意志、耐性和智慧,都是一场考验。他不得不在斗争的坚持中迅速作出调整,他把这叫作“周旋”“钻网”,叫作“带着枷锁的跳舞”。
题作《夜记》的系列作品之一《怎么写》劈头一句是:“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本来,对于自由写作者来说,“写什么”是不应当成其为问题的,此时居然成了问题。
1933年上半年,鲁迅还可以随时发表时评;及至下半年,形势陡变,则只好借谈风月而谈风云。正如他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他在文中大量使用典故、反语、隐喻,越过为语境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而奔赴目标。对付报刊忌讳他的名字,他使用并频繁更换笔名,乃至近百个之多,成为世界上使用笔名最多的作家。对于文中被检查官或编辑删改的地方,编集时他特意从旁加上黑点,或用黑杠标出,或在文末加写“附记”,且不忘在序跋中加以说明。
除了创作,他还十分看重翻译,从留下的文字遗产看,译文的分量甚至更大。他十分注重介绍苏俄,以及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对于苏联,也介绍著名的“不同政见者”如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同路人”的作品。他以译作直接介入中国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
譬如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故意撇下其中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不译,据他在后记里介绍,原因是原文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所以文学家和政治家是接近的。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上,鲁迅与作者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著名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过,“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因此他认为,“要维持现状”的政治与“不安于现状”的文艺不免时时处在冲突之中。
鲁迅不但从事著译,而且热心做编辑、办刊物、搞出版。他的目的,归根结底在改造中国这一点上。他要借刊物培养更多的战士,以集团的力量对付强大百倍的反动政府和专制制度。从在日本流产的杂志《新生》,到北京时代的《莽原》《语丝》,到上海的《奔流》《萌芽》《译文》等,可谓从不间断;此外还参与别的报刊的编辑,包括有名的《新青年》等。当他和青年朋友的书稿无法出版时,就搞地下印刷,诸如“奴隶社”“三闲书屋”之类的临时出版社,就这样搞了起来;而一批违禁的书籍,也就这样走出了地面。
出版图书的时候,无论著译,鲁迅都极其看重序跋的写作。他历来重视“边缘”,序跋也是边缘,从边缘进入中心。举例来说,像《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篇幅比正文长得多,其中虽然多是报章剪贴,却保留了文网史的大量故实;加上作者随机的批评,结果确如他所说,有了这样的“尾巴”,形象便见得更完全了。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曾几何时,一个高踞人民之上的威赫无比的政权,在一个早上黯淡收场;而希望自己“速朽”的鲁迅的作品,却在反抗它的斗争中获得了不朽的意义。历史悖论的力量如此,令人惊叹。
(《鲁迅:刀边书话》,林贤治 编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